在那麼多人的日記中,我最喜歡看小葉(正經時)、紹剛、中平、味味和雅君的文字,小葉的文字是那麼能引起我的共鳴(也許因為天性同樣傾向悲觀吧)、紹剛的生花妙筆、中平「入而不出,往而不返」的感情、味味感受的敏銳(可惜惜墨如金)、雅君的神來之筆常常讓我想幫他們出一本作品集。這裡引了其中三個人。小葉的話引自我大二下的日記本,那是我大學四年僅見最blue的一本(那時中平留下了「最後一篇」日記,還好不是絕響,否則真是大家的損失),卻也是我最愛看的。原因無他,還是那份真實吧!那時團裡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斷發生,日記本也如實地刻畫下了這段時光。
紹剛和味味的兩段則和我那年的巡迴有關。那年的期末公演是和師大合演,我們一起合練《豐收鑼鼓》和《秦王破陣樂》,由景雅菁老師指揮;我們自己又上了《月兒高》、《流水操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(肇寧彈的),還有兩首彈撥的曲子。除了《月兒高》外全是比賽完才練的新曲子,負擔之重可想而知。(那場音樂會評價最高的是由師大眾高手合演的《躍龍》〔胡登跳的絲絃五重奏〕,的確也實至名歸。但合演的幾首曲子我覺得表現得也很好)。不過繼「夠份量」的期末公演後,緊接著就是巡迴了,巡迴是以和承穎的獨奏會合辦的形式演出,內容又是幾乎全新的曲目(《流水操》《雲南回憶Ⅱ》上過,《二月》則是前一年巡迴時的回憶,《故鄉情》好像在哪演過吧,有點忘了),特別是全曲的《雲南回憶》----這首從來沒想過大學樂團可能演的曲子。但那時團練場地又有問題,所以最後刪刪減減只剩下五天可練,下場自然可以想見。複雜的節奏和反覆的樂節連我自己都感到迷惘,結果在台北場的第一樂章、台中的第三樂章都發生了嚴重的失誤,高雄場則是控制不住情緒,和團員發生了爭執(這是我指揮一年最大的遺憾)。於是這次巡迴,就在承穎加分,樂團扣分的情況下,平平地過去了……。
我從前也一直有「音樂最大」的想法,總認為音樂弄不好,什麼都免談。不過我最近才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。小葉回憶的是我大二下期末公演,由莊承穎指揮,小巨人獨奏的《秋韻》。那時演出的情況,的確就一如小葉所說的悽慘,和前次國華指揮、俊頤/立人獨奏的版本差遠了。如果音樂是一切,那麼這就是一切了。然而,真的如此嗎?即使在破碎、不完美的音符中,不也包藏著我們最私密的感受和回憶嗎?我看小葉、紹剛和味味的文章如此感動的原因,難道不是我們共同分享了這段回憶嗎?我想起《二月》承穎和恭羽清脆的柳琴聲,想起第一次練秋韻,不禁在路上哼著那綿長而含蓄的二胡主題、想起最後「思緒飄然」的尾聲,我當然也想起了《雲南回憶》,想起第一樂章那段纏人的笛子獨奏(SGB)、第二樂章如夢似幻的結尾、第三樂章方翎用兩(三?)顆定音鼓撐完、如君臨時披掛上陣,卻又表現完美的中笙獨奏樂段,當然還有結尾那瘋狂的響度……。假如是現在的我,現在的樂團,一定能演得更好吧!但是無所謂,生命哪裡沒有遺憾?就讓遺憾留在那裡,美好回憶的光芒卻不因這些遺憾而減損半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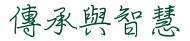 我下一屆的指揮是小葉,團長是鵝(方怡蓁)。說真的有些遺憾,我覺得在指揮的交接方面做得並不是很好。臼嗓卸任時,還留下了一份團譜的dBASE資料;承穎卸任時,也把指揮抽屜和譜整理得乾乾淨淨,在我任內還當助理指揮,幫助一開頭經驗不足的我。但是對於小葉,除了當一年的中級班指揮,還有巡迴讓他指《二月》和《水鄉歡歌》以外,我並沒有做太多經驗傳承的工作。但看他帶團練這兩首曲子時,我已經放心,比我第一次指《八月》和《冬月》(上次巡迴)要好得太多了!小葉當指揮的上學期,我一方面因為課業,一方面因為與某人的心理障礙,很少來社團,下學期就比較常出現,期末公演幫忙帶了彈撥小合奏(《姑蘇情》和《林中小憩》),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小葉獨奏的《塞外隨想》(小巨人指揮)和SGB的《白蛇傳》(小葉指揮)。不知小葉這樣的安排有沒有傳承的意思在?總之,SGB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未來社團的中堅。
我和小葉都拜何嗓為師學指揮(我大一也和劉宏一學長學過),這方面可說是國樂團傳承的一個顯著特徵:前任指揮通常自動地都會指導後進者,不是卸任了就走人,也不是想向下一任討首曲子指,純粹自願。許多卸任的幹部也一樣。這動機在哪裡?很難形容,但我想還是出於一份對這個曾經付出過的團體的熱愛,因而願意盡可能地貢獻自己的經驗吧!
以上所提是有形的一面,但無形的一面我覺得是更重要的:我們從大一進樂團以來,就看到那麼豐富的心靈,那麼充沛的熱情,他們的一舉一動,他們的歡喜或悲傷早就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腦海裡。這不是實質的經驗,而是更珍貴的東西----或許該說是一種精神的共鳴或感召吧!小葉曾在日記本上寫著:「或許十年前的人和十年後的人不同,但是關心的話題,面臨的問題卻如此相似。十年後的我們或許仍然沒有解決問題的智慧,但是堪可告慰的是:at least we are not alone!」或許,這才是真正的「傳承」吧!當你追尋前人的足跡時,時間被跨越了,空間消失了,這些美好的心靈和你是如此的接近;他們和我們的心已經都被國樂團緊緊地繫在一起,為這個團體或悲或喜;他們也和我們一樣,回顧著先人的足跡,在錯誤和學習中堅定地跨出每一步。
| 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